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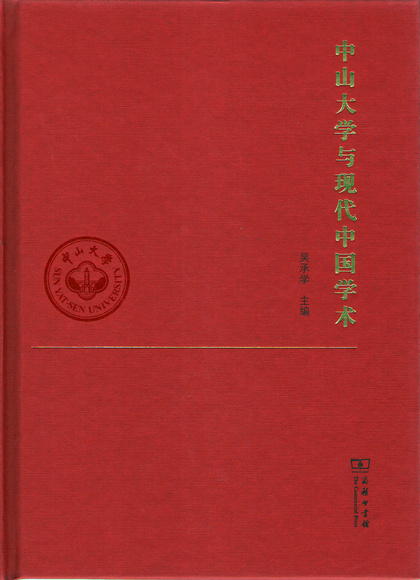
吴承学主编《中山大学与现代中国学术》封面
吴承学教授惠示《中山大学与现代中国学术》书稿,嘱我写序。该书稿洋洋百万馀言,一时难以遍赏。然走马观花,也可大致领略其佳胜。
今年恰值中山大学建校90周年,全校师生、校友怀着欣喜之心,以各种方式迎接校庆。吴承学教授主编此书,是一份切题而有意义的献礼。校史研究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比如以往有年谱、通史、散文随笔等,而此书另辟蹊径,以教育史与学术史为视角,广泛钩稽史料,收集深度研究中山大学校史、学科、学人的文献,以学理方式呈现中山大学与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关系,我以为,这是一种颇有深度与特色的校史研究方式。
读了这本书,我有一些感想。中山大学建校90周年,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它的建立与中国现代政治、文化、教育、学术关系之密切,却是罕有其匹的。中山大学1924年由孙中山先生手创,始为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先生逝世后,为纪念先生,遂于1926年更名国立中山大学。为实现中山先生“振兴教育”、“陶冶人才”、夯实“立国大本”的创校目的,几任校长如邹鲁、戴季陶、朱家骅、许崇清等勉力制定办学规划,科学完备学科建制,多方延揽优秀人才,使中山大学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办学规模一流、科研实力雄厚的著名高校。其时正值中华民族万方多难、亟需振衰起敝的时刻,但即使处于动荡环境,中大学人都不忘以“研究高深学问”为旨趣,追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治学境界;“革命不忘读书”、“要以学问求人生”更成为他们为人为学、贡献社会的坚定信念。他们坚信国家的发展,始终离不开科学的进步;大学的立校根本,始终在于学术。在学术处于新旧汰变、中西交通的路口,他们推陈出新、融会贯通,孜孜以求地致力于中国学术的现代化,为中国新教育和新学术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读了这本书,有一个问题引起我的思考:为什么中山大学建校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成一所雄居前列的高水平的综合性大学?我以为除了政府高度重视、重点支持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这是一所崭新的、没有历史负累的大学,大学掌门人以及许多教授具有强烈的现代大学制度意识和国际性眼光。这在当时中国大学之中,是非常突出的。中山大学自建校之日起,就以建设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为目标。1927年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议决的《大学规程》规定,高校分设文、理、法、医、农、工、商、师范、美术、音乐等科,须有两科以上方得称为大学,中山大学在1927年就完成了文、理、法、医、农五科的建设;至1934年增设工科,中山大学终成为“有统系的整个的中山大学”。学科建制的系统完备和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齐头并进,迎来了学校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当时的语言历史研究所、两广地质调查所、民俗学会、教育研究所、西南研究会、涵盖文法理农工医各科的中山大学研究院等学术机构,以及活跃于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现代史学派等学术共同体,都站在中国学术前沿,使中山大学成为影响深远的中国学术重镇。1952年院系调整,在中国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其文、史、农、医和社会、经济研究等学科力量,充实并促进中山大学的学术研究向着多元纵深发展。这些重要史实,在《中山大学与现代中国》一书中都有深入的研究成果。回顾中山大学精彩纷呈的历史,我们是有着深深感怀的,前人筚路蓝缕,我们后人应该追踪其后,发扬光大。
多年以来,关于大学精神的讨论是一个热门话题。我以为,大学的精神,主要是从一批大师、名师身上体现出来的。优秀学者是一所大学的灵魂。中山大学自创校以来就名流荟萃,大师云集。举要而言,文科著名教授有陈寅恪、朱希祖、岑仲勉、朱谦之、罗香林、梁方仲、刘节、鲁迅、傅斯年、顾颉刚、郭沫若、赵元任、容庚、商承祚、冼玉清、王力、詹安泰、王季思、董每戡、梁宗岱、钟敬文、冯友兰、杨荣国、王亚南、陈序经、杨成志、梁钊韬等,理工农等科著名教授有姜立夫、黄际遇、张云、罗宗洛、邓植仪、丁颖、陈焕镛、蒲蛰龙、陈国达、朱物华、卢鹤绂、冯秉铨、高兆兰、乐森浔、孙云铸、罗雄才等,医科有号称“八大金刚”的一级教授梁伯强、谢志光、陈心陶、陈耀真、秦光煜、林树模、钟世藩、周寿恺,可谓“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当然,限于篇幅,此书所选只是中山大学名家的一部分。借斑窥豹,已足见中山大学的精神气韵。中山大学学者以坚毅刻苦、开阔怀抱和创新精神,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启疆拓土,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为中国的学术发展贡献了聪明才智。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也是高尚人格的风标和大学精神的孳乳之源。他们身上体现着为振兴中华而献身学术和教育,谨守科学精神的优秀品质,也表现出由积学、修身而散发出的丰富才情和大家风采。对他们而言,立言、立德、立功其实是融为一体的。因此,我们既要继承他们的学术遗产,也要追慕他们的学人品格,和他们作深长隽永的心灵对话。
我注意到本书的编纂采用“详远略近”的方式,具体来说,就是对中山大学早期历史的研究收录比较多,对于晚近的研究则收录比较少,对于当下则没有涉及。从某种角度来讲,这是有其局限的。但我还是理解这种编纂方式,因为历史需要时间的积淀,也需要长时段与有距离的观察。对于离我们太近的人与事,评价起来有时反而不易公允、准确。所以从积极方面看,“详远略近”的历史研究方式对于当下的人们来说,既是一种期待,也是一种鞭策,一种勉励。中山大学的同仁们,让我们一起记住历史,传承历史,同时创造历史吧。
中山大学90校庆前夕于康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