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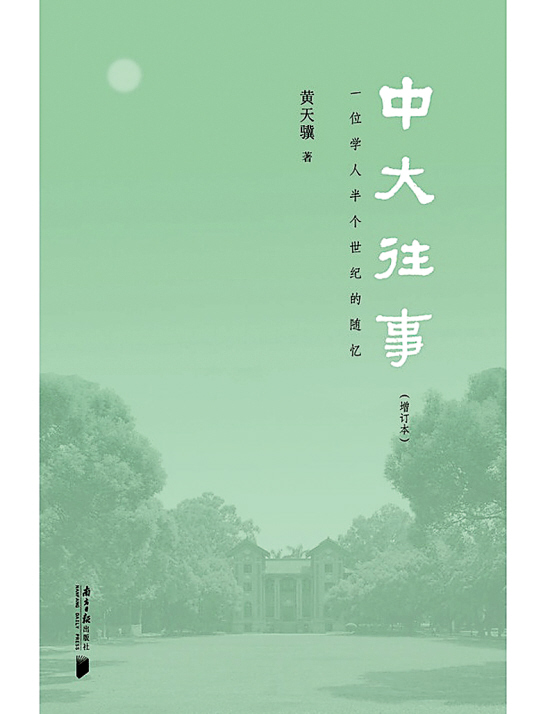
人事有代谢,回忆成古今。十年前,中山大学八十周年校庆,应友生之请,黄天骥教授撰写了《中大往事——一位学人半个世纪的随忆》一书,我则应《南方都市报》之约,写了一篇书评——《往事的追忆与精神的追寻》,从大学精神角度阐述其底蕴,虽然主旨不差,却未免随俗。十年之后,《中大往事》增订再版,增加了近十篇回忆文章,内容更形丰富了;我也步入中年,踏入回忆的河流,方始体味到,作者不随流俗沉缅往事或孤芳自赏,而是坚守人道的关怀与师道的传承,才最令人感佩动容。
作者在康乐园里工作生活六十多年来,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之中,颇历坎坷曲折,甚至遭遇惊涛骇浪,几至死里逃生,当然更有值得自豪,也让人引以为豪的光辉篇章。但是,这一切,书中几无一语及之,与坊间同类之作,大异其趣。在笔者看来,作者似乎是始终站在一个教师的立场和角度,述往事以启来者。
虽然有名言说:大学者,大师之谓也。其实,更有名之言当是至成大圣先师孔子所言的“仁者,人也”。在过往的几十年里,如何坚守人的尊严与品格,才是最核心的问题;没有独立人格尊严的养成,学生难以成为良材,学者难以成为大师。比如书中有一篇《小人物》所写的老陈和老董,都曾是有才华的青年教师,尤其是老董,初出茅庐,即有卓异表现,奈何遭受非人待遇,倍受摧残,以致英年早逝——如果能多得到一些正常人的待遇,他们或许早成大人物了。最突出的是“小人物”张其,不迟于卓炯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但卓炯被评为特等模范,成为大人物,张其却以副教授终其身,始终只是个“小人物”,而攻击批评甚至打击陷害他的人也踩着他高升了教授,有的甚至变成了“大人物”。对此,最爱才心切、也备受尊崇的老校长黄焕秋,就曾非常尖锐地指出:“不爱护、不保护人才,这在我们学校是有惨痛的教训的!大家想一想,张其的情况是怎样的!”而作者在回忆黄老校长时,却只用了“好人”一词——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好人,并不容易。
作者在回忆他的老师辈,一些真正的学界大人物,像容庚、董每戡、詹安泰、黄海章、王季思等先生,并没有强调他们如何成为学术权威,如何给自己“加持”以彰显身份,而是强调他们在非常时世中对于人性的可贵坚守。比如容老曾经把早请示、晚汇报、背毛主席语录称为“三座大山”,在林彪外逃之后,更发惊人之论:“这是搞阶级斗争的结果。你斗我,我斗你,就斗成这个样子。”而在改革开放后,又“老夫聊发少年狂”,与王季思先生比赛谁先入党。这看似矛盾的情形,恰恰反映了他们身上的人性之常或常人之性;没有对这人性之常的坚守,孰能至此!作者的业师王季思先生一度因为“思想”压倒人性,对人对己均造成过伤害,而其“补过”,也正是通过人性的回归与张扬。比如,当他知道一位中年教师,因为文革期间历经坎坷,久疏讲台,待到重登讲台,讲课效果不甚理想,同学们辄有怨言,便特意亲往随堂听课,并在课间几次上台亲手为这位老师擦黑板……这一幕,感动了同学,也感动了任课教师,令同学们“一辈子也忘不了”——许多同学说:正是从王季思先生身上,“懂得了怎样做人,怎样助人,怎样教书育人”。
这次增订的最大亮点之一,是辑录了作者三十年多来,以浅近清雅、骈散兼行的文言文为学校所写的二十多面碑记,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大改革开放发展的光辉历程,堪称岭南一绝,也同样彰显了一种守正持平的人性光辉。例如《“碑记”后面的故事》中,讲上世纪八十年初,中大接受香港梁銶锯先生捐建学校的大礼堂,是1949年后中大、也是全国首次接受以海外实业家命名的建筑物,学校方面决定立碑纪事以为投桃报李。在以最高规格请动商承祚教授秉笔书丹后,由作者负责撰文。传统的碑颂之体往往多浮词谀字,要写得落落大方,委实不易。作者已经是费尽心思,可还是被商老中途“罢了下工”,因为发现了一个他认为不够准确的成语——德高望重——“望者,名望也。我未听过梁先生的名字,怎能说‘望重’呢!”作者反复解释,又连哄带求,商老就是不肯写,直到急中生智,改成“龄高德重”——八十之年,是谓龄高;支持教育,是谓德重——商老才把碑记写完。在几十年曲折岁月之后,如此执着于求真求实,岂容易哉!人格独立之尊严由此彰显。
所以,作者心目中的师道尊严,乃是要求教师(大师)应该首先是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明师”:不仅明智、明慧、明察,重要的是心怀像水晶一样透明;澄澈的人性光辉,可以使愚者智,懦者起,可以帮助人洗涤灵魂的污浊——只有坚守这样的师道尊严,才能让一所大学精神传承,长盛不衰。
原文链接: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15-02/01/content_64205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