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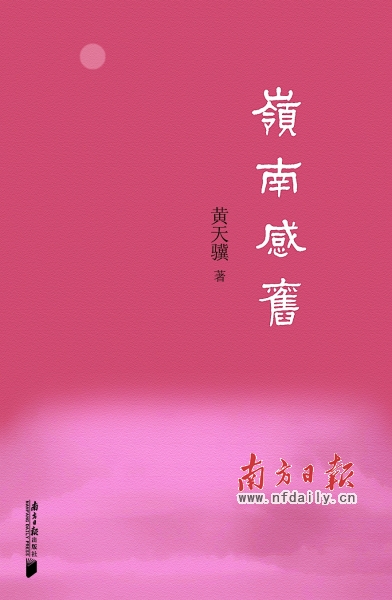
《岭南感旧》
黄天骥 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2年8月
定价:38.00元
《岭南感旧》有一篇《市声》,从市井各种叫卖声谈起,谈到茶楼酒肆伙计与顾客如何互动,当时招呼交易用的俚语方言以及肢体语言,如“埋单”的动作表达与语言含意等,瞬间将人引回历史现场,这种现场感,也活化了相关的民俗风情。只有这种活化的东西,才能让人记忆深刻,才能使文化得到真正传承。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真正能否行得远,也还得看“言”之背后所承载或附丽的人、物、情、事。近现代以来,岭南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全方位崛起,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至深,而岭南文化以及岭南形象,仍乏足资树立之点面;岭南文化,卑之无甚高论,至少特点鲜明,足以让人难忘。究其原因,或乏于事乏“言”,或言乏于文。有鉴于此,土生土长,既有西关大少体验,如今亦是一介平民的著名学者,著述之暇,应约撰《岭南感旧》数十篇,刊之南方都市报“大家”栏目,于今结集出版,载动岭南记忆,可谓做了功德。
对于地域文化,我发现各地都在奢谈,是高谈阔论,都是历史如何悠久,人物如何杰出,文化如何优秀,抽象的多,具体的少;片面的多,全面的少;口号的多,生动的少;往往似是而非,听起来一头雾水——这本身就是无文化的表现;在此风气之下勃兴的民俗文化,理应不犯这些毛病,往往也难以免俗。如我所谈则异如是,黄天骥教授所谈更异于是。《岭南感旧》有一篇《市声》,从市井各种叫卖声谈起,谈到茶楼酒肆伙计与顾客如何互动,当时招呼交易用的俚语方言以及肢体语言,如“埋单”的动作表达与语言含意等,瞬间将人引回历史现场,这种现场感,也活化了相关的民俗风情。只有这种活化的东西,才能让人记忆深刻,才能使文化得到真正传承。
然而,《市声》不止于此,它还记录了“市声”的时代变迁,市井声音也会因时代而变,也会反映时代的变迁。比如,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茶楼“揸住细莲,两个大奶”的吆喝,到五六十年代变成掏出《毛主席语录》读最高指示的“静默”;马路上“磨铰剪——剪柴刀菜刀”的叫唤变成如潮的难耐又难挡的车流声,这种市井小民的众声喧哗所反映出的时代变迁,才是真实的时代变迁,才是真正的“群众主义”,才真正能让人在美好的回味中“追寻美好的未来”。当下最令人纠结的节俗问题,作者也常常能让你回到从前又不止于从前。比如《八月十五竖中秋》,做灯笼、插幡竿、挂灯笼这一岭南“竖中秋”的民俗,今人多已隔谟,听作者讲起来,自然津津有味。但是,有过家破人亡的抗战经历的人,尤其是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与古典诗文写作,满腔满盈“中原北望竖旌旗”的历史积淀的人,怎能不在游行声浪的盈耳喧嚣中,别有幽怀通古今呢?
在市井民俗而外,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对于师友的回忆与感怀,更能见出作者的本色,也更能触动读者的情怀,也才能丰富“感旧”的内涵,增强“感旧”的层次感。这方面,作者也没有脱离“岭南”特色,也贯穿了其做学问的本色——论文从最微观的材料说起,卒章见其大端;散文从最日常,最能让人忘记同时也最能让人记住的细节写起。比如他感怀教育环境的变迁,从中大的草坪写起。岭南草坪,四季长青,尤其是中大草坪,冠绝中国——当年我一位同窗大冬天从北大南下,一看到中大草坪,就决定到中大继续深造。可这块草坪,曾几度铲起,或被红卫兵改做翻身广场,或用来种红薯,最后还是成了照毕业照的最美场景。又如岭南戏曲,作为古典戏曲研究的权威,作者不吊书袋,而是从音与调说起,说当年的戏曲就像粤港的流行歌曲,先是中原音、中原调,后来改用白话,乐器与调门自然也跟着变,到如今,还出现了粤剧与流行音乐互渗的情形,那是愈益的岭南化了。
即使写自己的老师,写那些大学者们的时代际遇,作者还是能从岭南什物着笔。蛇被称为广东异味,“食在广州”也肇兴于“太史蛇羹”,《吃蛇羹和“蛇”出洞》,就从吃蛇羹写起,写那帮吃蛇羹的一代人师,如何被那特定的社会“吃进去”又“吐出来”,成为一帮“牛鬼蛇神”。而这种“牛鬼蛇神”,旧的“时代先锋”口中的“美味蛇羹”,转眼之间又成为“新的时代先锋”与“精神导师”。如此一翻覆,怎能不搅得你五内俱热,难以忘怀?从岭南出发,从岭南风物出发,身世家国,融于笔端,“触物兴物”,也能“篇终接混茫”,如此文章,载动岭南记忆,无愧时代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