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核心提示
高华年(1916年—2011年),福建省南平市人。高华年他曾是岭南语言学界的领军人物,也是中山大学对外汉语教学的奠基人。
一生潜心研究语言学,尤其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面有很高的造诣。生前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最高寿的老教授,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曾长期担任广东语言学会会长。他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学习他生前的著述,由他的夫人植符兰副教授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把他失散于全国各单位的论文收集在一起,编成《高华年文集》,近日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高华年师从罗常培和李方桂,加上西南联大所在地昆明四周的少数民族众多,为高华年成为大师创造了外在条件;而他拥有的那双无比灵敏的、能够分辨出人类最细微语音差异的耳朵,则为他成为语言学大师提供了天然的内因。
而今大师虽已离去,但他留给我们的思想依然散发着强烈的光芒。翻开即将出版的《高华年文集》,你会发现其中很多研究内容,都拥有着无可估量的巨大价值。
■ 关键词:才华
一代宗师,才绝惊艳
年轻有为。这四个字可以说是对高华年在20多岁时便已取得相当学术成就的最好注解,而走上语言学研究这条路,是他一辈子的选择,从未改变过。
和民国时期很多学术大师一样,高华年在进入大学之前,走的也是新派小学+教会中学之路。而这种模式也决定了他在国学和英文方面,都有着相当不俗的造诣。高华年之子高植生回忆说:“我的七叔曾经告诉我,父亲在中学时就很严谨,他的笔记本,每一个本子都是很小的字,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是写得满满的。”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高华年年轻时并没有想过从事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最早的时候他应该是想成为一名教师。所以中学毕业后,他就去报考了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而根据高植生的说法,父亲是在北师大期间,受到黎锦熙教授的影响,才开始立志“研究学问”。虽然在这期间,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北师大被迫迁到西安,但这并没有影响到高华年的志向。毕业后,他报考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辗转了很久才从西安到达昆明。而在此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已经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
在文科研究所里,高华年得到了罗常培、李方桂两位中国语言学界泰斗的指导。两位大师震惊于他那过人的听力,开始“因材施教”帮助他向语言学方面发展。这期间,由于昆明四周少数民族众多,高华年就开始对云南的黑彝等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深入调查并写出报告。也正因为这些成就,1943年1月,罗常培写信给冯文潜教授,推荐年仅20多岁的高华年在毕业前就开始到南开大学的边疆人文研究室工作。推荐信中不乏赞誉之词:“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高华年所做昆明附近一种黑彝语研究已经完成,全稿达十七八万言,内容分音系、借字、语法、故事、词汇五部分,关于借字之分析及语法之结构均为前此中外学者所未道及,至于材料之丰富,记音之准确,弟(罗常培)审查之后已可负责保证其可靠。”
1944年,高华年的《昆明核桃箐村土语研究》一文获当时的教育部嘉奖,同时获奖的还有闻一多、陈寅恪、冯友兰等这些当时已成名的学术大师。刚毕业的高华年能得到此奖,足可以证明他这篇文章的学术水平之高。
由于“天赋异禀”,凡是人类发出的声音高华年都能听出其不同,在听音、发音、辨音方面是当代第一人,即使到了垂暮之年,功夫犹在。即将出版的《高华年文集》收集了很多他年轻时候写的文章。经历了60多年的风雨洗刷之后,有些文字已经模糊不清了,只能影印出来。高华年的夫人植符兰说,很多高华年亲手写的声韵,语言研究和少数民族调查的材料,“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写不出来”。
还有一个事实也能说明高先生的独一无二。他在中大中文系前后开了七门课,但因为他不在了,有些课比如《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汉藏系语言概要》,中文系已经开不了了。并不是没人想学,而是很少人在听音、辨音等方面能有高先生这样的造诣。当然,除了这种天分之外,高华年的勤奋也令人吃惊:穷尽一生收集到的海量的调查材料,包括很多卡片、笔记本,单是收集在《高华年文集》中的数量就已经非常庞大。
■ 关键词:风骨
低调内敛,明辨是非
从民国时期一路走来的学者大师们,大都有一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高华年作为其中之一,自也有其可敬之处。
作为书生,高华年从来都不乏那倔强的嶙嶒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高华年随南开大学搬回天津。途中在重庆候机北上时,他于7月17日得知闻一多教授在昆明被刺的消息,极为愤怒,并和西南联大滞留重庆的33位教授,包括金岳霖、姚从吾、马大猷等一起致电南京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要求主管当局务必缉凶归案,严究主使。“一代通才,竟遭毒手!正义何在?纪纲何存?同人等不胜悲愤惊愕!”教授们的痛斥让社会舆论更加沸腾了,也使蒋介石陷入了整日的“忧闷”,最后被迫下令让刚上任全国警察署署长的唐纵前往昆明办案,并声称该案为“政府莫大之耻辱”。
作为书生,高华年同样有那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热血时刻。在联大的岁月里,高华年和所在班级的同学经常到罗常培先生家做客。虽然时已至深夜,但胸怀天下的年轻人在讨论问题时还是会遏制不住憋得火热的喉咙,争论声大作。恰好当时陈寅恪先生住在楼上,于是有时候就会听到陈先生用拐杖敲地板“笃笃笃”的声音。这时罗先生就会说,“陈先生要休息了,你们快回去吧”。众人才作罢散去。
作为学者,高华年的政治判断同样准确。随着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的溃败已无法挽回,1949年天津的国民党政府决定撤离,同时准备好了飞机让大学里副教授以上的教师离开,但高华年最后选择了留下。经过几十年的风雨磨砺之后,当被问及当年为何不跟随国民党去台湾时,他也只是云淡风轻地说一句“当时就是不想去”。此后,高年华在1950年南下广州,先在岭南大学任教。在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合并后,他就一直在中山大学语言系任教授,这也是中国的第一个语言系。在1954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大部分语言系的师生合并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高华年本也想去北京大学,毕竟他是北大的校友,同时他的导师罗常培以及很多朋友也都在北京。但那时他正陷入热恋中,同时考虑到在广东更适合做少数民族和方言的研究,便选择留在了中大,并一直任语言学教研室主任至退休。几十年来,他为中国的语言学界培养了无数的人才,包括著名音韵学家唐作藩、著名方言学家詹伯慧等。
作为学者,高华年的低调谦逊也是很著名的。弟子们总结高先生长寿的秘诀是:淡泊名利,清心寡欲。他的弟子、韩山师范学院院长林伦伦说:“先生低调内敛,除了上课做学问,几乎没有什么应酬活动。他不争名利,60岁退休年纪刚过不久就辞去广东语言学会会长等职务,让位给年轻人。”
■ 关键词:专注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有人说高华年一生都表现了一个语言学家的书卷气质,这是对一个学者能在浮躁的时代里始终安心进行学术研究的褒扬。对于交际和热闹场面的排斥,使得高华年乐于将自己锁在书房里,与尘世的纷纷扰扰相隔离,悠然地修改自己的作品,看学生的文章,帮别人写序。每天除了与报纸和书为伴之外,高华年对其他的一切无甚关心,家里的事情也从来不管,甚至连自己一个月有多少钱的工资都说不出。
高华年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文章写好、修改好,将来结集出版后留给后世的人。因为已经90多岁的他将名利看得淡如水。
高华年最显著的学术成就便是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成果,其中1958年出版的《彝语语法研究》(科学出版社)无疑是其代表作,在他的墓志铭上便刻有这本书的名字。这是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彝语语法的著作,在分析彝语的语法现象和规律方面富有独创性。语言学界对这本书评价很高,国外学者已经翻译为英文本,影响很大,至今仍是国内外汉藏系语言研究的主要参考书。
除此之外,高华年还研究过印尼语。曾有一个年轻的印尼人做他的发音人。他仔细观察那个人一段时间后,开始尝试着发音,然后再找一个印尼的专家核对一下发音是否准确。后来他写成了两篇研究印尼语的文章,分别是《印尼语的句子结构》和《印尼语的名词结构》。
在对广州方言的研究方面,不得不提高华年的著作《广州方言研究》,这本书前后经过近20年的动荡之后才最终出版,该书名也镌刻在他的墓志铭上。作为高华年的夫人,植符兰是广州地道的西关人,自然而然就成了高华年的广州话发音人。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高华年一共搬过十几次家,使得有些珍贵的材料不免在奔波中遗失。后来遭遇“文革”,红卫兵抢走了很多他的教学笔记和文稿,他自己则被遣送去英德的五七干校。“当时我们不敢作声,现在想起来很痛心,那些资料如果能保存下来,现在就是无价之宝了。”植符兰说。
“文革”结束后,高华年很快就集中起精神,继续他的语言学研究。到了1980年,《广州方言研究》终于在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得以出版。其中有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学生去香港找到商务印书馆,说高教授有这么一本书,没想到他们马上答应出版。这本书是高华年的第二本代表性专著,也是内地第一本系统研究广州方言的书。书的内容丰富,包括语音、语法、词汇和小说故事等四个部分,重点放在词法的分析上,本书对于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汉语史的研究和汉藏系语言特点研究等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在海内外影响很大,是现在粤语语言研究不可绕过的一本书。
严谨的作风是高华年功成名就的重要原因之一。1981年中大的汉语培训中心正式创办时,高华年任主任,当时只有6个美国学生和一些年轻老师。有人建议直接请几个北京人回来稍加训练后便可进行教学,但高华年坚持认为,虽然会说普通话,但如果没有经过中文系基础课的训练,便不能当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所以高华年让那些年轻老师去中文系补课,直到考试及格了才能回来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最后,当初只有6个学生的汉语培训中心,现在已经发展成为1000多人规模的国际汉语学院。毋庸置疑,高华年是中大对外汉语教学史上的第一人。
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论文会被高华年打入冷宫。他写过一篇青苗语的论文,但却藏了很久。经过反复研究、修改之后,在几年前他才放心把文章发表出去。他的很多“未发表”的文章就这样安静地躺在角落里。在90多岁的时候,他还在想着如何打磨这些文章,以期给后人留下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精华荟萃 传世珍宝
《高华年文集》全书分为三大部分:论文、手稿影印和附录。
第一部分论文选集共收入论文32篇。内容包括:I.少数民族语言论文八篇,如:纳苏语中汉语借词研究;杨武哈尼语初探;青苗语音系;彝语的重叠词、同义词和同音异性词;纳苏语的附加语;汉藏系语言中几个特殊语音;汉藏系语言调查研究法。Ⅱ.印度尼西亚语2篇:印度尼西亚语的句子结构;印度尼西亚语的名词结构。上述这些语言过去没有人研究和发表过,是高先生甘当拓荒牛,白手起家,第一个进行田野作业,深入调查研究而后整理撰写出来的。
这部分除了对具体的某一语言进行研究、描写、阐述外,还有一篇《汉藏系语言调查研究法》是高先生多年来调查、记录和研究众多少数民族语言的心得体会和经验结晶,这是从事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的指导文献,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难能而可贵。连同他出版的两部专著《彝族语法研究》和《汉藏系语言概要》来看,称他是少数民族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一点也不为过。
Ⅲ.方言,收入论文6篇:方言与方言地理学;粤方言研究:回顾与展望;广州话形容词重叠的作用;粤方言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粤方言拼音方案中文和英文;粤方言与普通话的比较。这些论文都是高先生几十年来在广州深入调查、研究粤方言的心得结晶,连同他已出版的专著《广州方言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该方言的巨著)来看,他对粤方言不但情有独钟,而且见解独到,挖掘深刻,辨析细微,不愧为粤方言研究奠基之巨著。
Ⅳ.语言理论,收入论文6篇:语言和言语没有区分的必要;语言学的学习与研究;文学语言与文艺作品语言;论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语言、言语和思维的相互关系;关于语言研究的几个问题。从这些文章连同他的专著《语言学概论》可以看出高先生的语言学功底有多么的深厚。他悟出了一条真理:博而能精,是任何一个做学问的人必须经过的过程。在这些文章里,他对语言的起源、语言的本质、语言的功能、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发展的规律包括内因与外因等都阐述得十分透彻而精辟。对人们学习、研究语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Ⅴ.汉语教学与研究,收入文章10篇:汉语拼音方案的优点;试以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相结合的原则论汉语兼语式问题;对外汉语教师应具备的条件;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一种方法;汉语的塞擦音;汉语的声调等。这些文章涉及到对外汉语教学的方方面面,既提出了教留学生的教师应具备的种种条件以及如何去创造这些条件,又提出了留学生学习汉语的方法以及重点与难点,密切联系实际,又突出了重点,使读者看后甚得要领,对提高和发展对外汉语教学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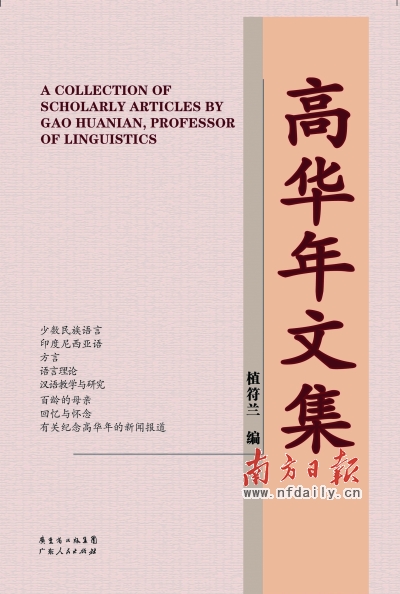
《高华年文集》
植符兰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年5月
定价:88.00元